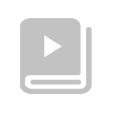1、 社会认知的多样化与自我认知的茫然性
伴随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打造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国内民众已由原来单一的对经济进步的强烈需要转到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进步、社会事务的公正与公开等多方面的强烈需要,同时,伴随大家思想的开放,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也走向多样化,从而对社会的行为、风气、进步有着多样性的认识与歧异的怎么看。需要看到,这种社会认知的多样化包括着公众自我认知的很多不确定的原因,譬如社会公众对待所发生的暴力犯罪现象,常常是一方面对公安机关打击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一定,其次又怀疑公安机关防控、打击不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定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警匪一家”、“姑息养奸”。社会认知的多样化与公众自我认知的茫然性,总是使得很多人对自己眼前和将来在社会上的安全地位抱有不确定感,这种情绪极易感染,一块暴力事件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大概在公众之中引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茫然的行为表现。
2002年4月,江西九江接连发生两起饮食摊点投毒案,一时间,市民几乎谈“食”色变,甚至不敢到所有些饮食摊点及餐馆用餐,大量早点、餐馆因之而门可罗雀。针对这种情况,九江公安局当机立断,准时召开全市媒体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了案件事实真相和抓获化名“张学友”的犯罪嫌疑人的详细经过,从而准时澄清了各种谣言,获得了市民的共识,社会上也因此非常快恢复了往日平静。
2、保护公信力与拓展信息途径
社会学觉得,社会上正常的信息途径一旦遭到了阻塞,公众之间的流言就会产生,而流言传播的内容则主如果肯定时期内在社会上或群体中互有关心的消息,这种消息一般又与大家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或者与个人与群体利益有着间接关系的。对于社会治安方面来讲,因为任何违法犯罪现象都会多少对公众导致心理上的阴影甚至是利益与生命的直接损害,而暴力犯罪尤为甚之。故而,公众对暴力犯罪有关信息极为关注,公安机关假如仅仅满足于“关门办案”、“闭门抓人”,而不愿向公众准时透露案件的有关真实状况,就大概引发社会流言和公信力危机。从几起典型的连环杀人案在公众之间的种种传播来看,就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
2003年11月14日,河北《燕赵都市报》以《65条人命恶魔在沧州落网》为题,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立即引来各家媒体及各大网站的很大关注,很多民众纷纷追问:为何不早一点向大家通报案情?为何没能早一点破案以至于被杀这么多人?为何不早一点向大家公众提示自我防护手段?为何不相信公众对犯罪信息的判断力?法新社甚至就此事报道说:“让人担心的是,近期破获的几起谋杀案说明,中国警方觉得无需向公众通报连环杀手案件”,该报道觉得,假如警方及早向公众通报连环案,民众既能够加大自我保护,还可以给警方提供线索,“但警方没这么做,杀人者得以继续行凶”,“中国政府向来不愿透露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的信息。中国的犯罪数据没完全公开,只有已经破获的案件才会在很多有关犯罪活动的电视节目中得到报道,那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展示警察的工作。”
“不愿透露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的信息”势必导致“公众恐慌”,从而引发公信力降低,同时也决非是“从积极的角度展示警察的工作”。
2003年2月6日,广州“非典”进入发病高峰,广东全省发现“非典”病例218例,《羊城晚报》2月15日以题为《手机短信流言纷飞 报纸电视稳定人心》一文谈到:2月十日晚,广州由于大家竞相用手机传递疫情信息而导致互联网瘫痪,疫情信息的传播远远超越了病情本身。
2月12日,广州场甚至出现了大米、食盐、食油抢购现象,有些企业乘机哄抬物价。这样来看,社会每发生一块重大事件,假如公众没得到政府权威部门准时、准确的信息引导,公众之间的流言便会越传越多,越传越广,日渐地也越传越不靠谱。基于这个道理,当社会上发生暴力犯罪案件之时,公安机关就应该准时站出来以事实说话,如此,公众之间无论是多么绘声绘色的流言,都将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这就需要大家需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大力拓展信息畅通途径,把公众欲知、应知、早知的信息准时、准确、完整地告诉公众,保护公安机关自己的公信力不受损害,并相信公众对暴力犯罪的剖析和分辨案件信息的能力,相信他们对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某地一纺织厂附近,短期内接连发生数起晚上下班的女职工遭歹徒强暴的案件,公安机关就应在一面加强办案力度的同时,一面准时告之附近女职工歹徒作案的特征、时间、体貌特点、人数等等,以提醒她们加大戒备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手段,并随时向公安机关提供所学会的所有线索。事实证明,如此做,既能够帮助公安机关及早破案,又有益于统一社会认知,形成打击合力,这才是真的意义上的“从积极的角度展示警察的工作”。
[1][2]下一页